狗儿睡在床上继续想着豹子哥,回味起昨晚跟豹子哥在床上的情景:
感觉豹子哥睡着之后,他装着无意中抬了一下手,从豹子哥的下面慢慢滑过,硕根的蓬勃,勾起了他强烈的欲望。见豹子哥没有动静,忍不住又悄悄地将手向豹子哥的下面伸去,心里狂跳着轻轻地抚摸,探求着它的硕大、坚硬和热度,品味着它的质感,想象着它傲然的形状,沉浸在偷来的心理快感中。豹子哥动那一下,给他吓坏了,生怕豹子哥醒来跟他翻脸,幸好豹子哥没醒,只翻了一个身。
半夜时,让豹子哥的腿压醒后,发现豹子哥侧着身子抱着他,健壮的肉体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一双粗壮的大手把他搂着,下面硬硬的硕根顶在他的腿上有节律地勃动着。狗儿一动不动地躺着,沉溺在豹子哥的怀抱里,静静地听着豹子哥平稳的呼吸,感受着豹子哥有力的心跳,呼吸着豹子哥散发的雄性体味。狗儿愿时间就在这一刻停止,永远留在豹子哥的怀抱里。
狗儿回味着与豹子哥裸拥的滋味进入了梦乡。朦胧中,豹子哥戴着大雁照片上的那顶军帽,牵着他的手欢快地走在打猎的路上;恍惚间,路上多了大雁,军帽回到了大雁头上,大雁嘴里含着一截竹子吞吐着吹奏,吹出的是“咚咚喹”的声音,他们又是在去豹子哥的家的路上,豹子哥背着他,他下面硬着顶在豹子的两条背肌间;迷幻中,豹子哥赤身祼体背着他趴在床上,下面的坚硬嵌进了豹子哥深深的股沟里。狗儿魂悸魄动,酥麻感从坚硬的深处向周身扩散,一股股的液体从下面喷射而出。
狗儿在喷射中醒来后,清醒地感觉下面还向外喷射了好几股。惊诧了一会,试探着向下面摸去,触摸到的是一种浓稠的糊状液体,肚子上有一些,床单上有一摊。这就是的男人的精Y?狗儿以前不止一次听大男孩说过这东西,还听说“人”就是这东西形成的,是男人给这东西射到女人的肚子里,装进了女人肚子里的那个人形模具,就慢慢地变成了人,这小人长到一定程度,就生了下来。
狗儿觉得他现在也可以弄出“人”来了。再一想,以前听别人说做梦S精,是梦见跟女人在一起,那东西刚一顶到女人下面,就开始射了,还对没梦到插入的滋味很感遗憾。他怎么梦见的是豹子哥呢?觉得自己有些奇怪。再慢慢地回忆刚才的梦境,梦中与豹子哥的接触很飘忽,只有下面嵌入豹子哥股沟里那一下感觉很真切。也就是刚一嵌入,就射了起来,这一点好像还和别人“刚一顶到就射”是一样的。
以后跟豹子哥睡在一起,下面贴进豹子哥的股沟里,会射出来吗?豹子哥梦见过我吗?梦见他那东西贴进我的P股沟里,他会S精吗?他能在醒的时候让我爬到他背上,或是他压到我背上像梦里那样做吗?狗儿在想入非非中重新进入了梦乡。
早上醒来,狗儿揭开被子,查看夜里喷射出的东西。床单上有两小块明显的迹印,摸上去稍微有些硬的感觉,有点像做鞋子用的布壳一样。狗儿叠好被子,压在那两块迹印上,担心蛮牛和妈妈发现自己的隐私,更怕他们发现后,问出让自己难堪的话来。好像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心里惶惶的。
大雁吃过早饭,就到蛮牛家去找狗儿,路上摘了几片树叶放在衣兜里,去“教”狗儿吹“咚咚喹”。其实他自己也明白,吹“咚咚喹”跟吹口哨一样,全靠自己去悟。但要和狗儿在一起,有个借口总要好一些。
狗儿一人在家,正想着趁着蛮牛和妈妈不在家时,怎么给床单上留下的迹印处理掉,见了大雁来,就只好作罢。搬来板斧(违规词)请大雁坐下后,又转过去泡了一盅茶端给大雁。见狗儿对他这样礼貌和热情,大雁心里热乎乎的。
“你照片上的那顶军帽还在吗?”狗儿想到昨夜的梦境。
“呵呵,那是照相时找别个借的,那个时候有一顶军帽戴起,觉得就是最神气的了!”大雁由军帽聊到那个年代在县城里见到的时尚,聊到演出场景和演出前后的花絮。话题一打开,看到狗儿很感兴趣,就不提教“咚咚喹”的事了。
蛮牛挑着水回来看到大雁跟狗儿聊得神采飞扬,很是诧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雁什么时候喜欢和人‘摆龙门阵’了?这么多年还从没主动来过我这里!”虽然热情地招呼着大雁,还是不由地多看了他们几眼。
大雁找了一个来去的借口:“蛮牛,给你钉锤借用一下,我柜子门松了。见你不在家,怕狗儿找不到,就在这等你”。“要得,我去给你拿”蛮牛转身进屋拿来钉锤。“我回去了”大雁接过钉锤,看了一眼意犹未尽的狗儿,转身离去。
“狗儿,你妈在水井湾上掰包谷,你去接她回来。”蛮牛的话,让大雁感觉是蛮牛看出狗儿想跟他一起去,故意给狗儿支个事,好让狗儿别跟他在一起。
由对蛮牛的猜疑,大雁联想到刘家三兄弟后来跟自己的关系。
在刘幺毛失踪的那天晚上,他悲痛欲绝,五脏俱裂,疯了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刘幺毛,到了最后昏倒在路边。天黑后,娘见到出去分头找刘幺毛的人陆陆续续地回到家里,想着他头天去挑水“踩虚脚了,摔到坎下”,到去找刘幺毛之前,还一直躺在床上,水米未进。不放心他,就找到了刘家。后来是刘家三兄弟在老鹰崖找到他,一路上轮换着背他回来。
在他躺在床上养伤那十多天里,刘家三兄弟轮流着给他家挑水、砍柴,还把他家地里成熟的包谷收了回来。对刘家三兄弟在他养伤期间给予的帮助,娘心里很是感激,也帮他们三兄弟做一些缝缝补补的事。
伤好后,第一次去挑水回来路过那片树林时,看到刘大毛站在路上,好像是在等他。走近后,刘大毛表情迟疑,语气急促地说:“大雁,累了歇口气吧,和我到里面去。”说完,转身朝林子里走去,刘大毛走了一段见大雁没跟他来,转过身停下来看着他。
他当时想:刘大毛不会是想做那种事吧?要是让他做了,说不定以后二毛和三毛也会同样要他这样,那他成什么了?必须坚决地拒绝!
迟疑了一会,还是硬着头皮,忐忑不安地跟着刘大毛进了林子里去。走到林中一小块空地,刘大毛找了一个地方坐下后,他见刘大毛还没有要做那事的意思,也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唉……事情不出也出了,我们几弟兄气头上做了过头事,幺毛现在也死活不知。‘冤家宜解不宜结’今天想好好和你说一说心里话”刘大毛长长地叹了口气,带着懊悔的口气说道。
“愿意说心里话吗?”刘大毛见他沉默着,追问道。他点了点头。
“你和幺毛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怎么说呢?就像亲兄弟一样,可能比亲兄弟还要亲。他不见了,我心里可能比你们还要难过,如果说真的要死,我宁愿替他。”
“你对刘幺毛的那种情份,找他那天,我们都看出来了。要不然,那天晚上不会去找你,你睡在床上那几天,也不会去帮你家做事。”
“你们真的做过那种事吗?”两人沉默了一会,刘大毛又问。
“嗯。”
“都愿意?不痛吗?我看那天你痛得不得了,还流血了。”
“是愿意的,不是像你们那样做的,也不是痛得不得了。不问这个了,好吗?”
“好吧,不问你和幺毛做的事了。你说说,冉老二和吴三哥,他们晚上都是睡在一起,别个说他们比亲兄弟还要好,他们也是像你和幺毛一样吗?”刘大毛换了对像,但话题还是没离开那种事。
“不晓得。”
“我娘还在等我挑水回去煮饭。”看见刘大毛的裤裆明显地隆起,他怕刘大毛接下来会向他提出那种要求,找了一个脱身的借口。
“好吧,就说到这里,今天我们说的话,哪里说哪里丢。你放心,那事我对二毛和三毛都打过招呼了,不会说出去的。开始是以为你欺负我家幺毛才做出那过火的事,幺毛现在死活不知,我们几弟兄也很后悔,以后不会为难你的,你也不要记恨我们。看在你和幺毛的情份上,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事,说一声就是了。”
“我不会记恨的!”他如释重负,说完就朝林子中的小路走去。刘大毛还坐在原地,也许是裆中的隆起还没消退,不便起身吧。
这么多年来,刘家三兄弟还真没难为过他,也没说出那事。路上遇到了,他实在磨不开时,还相互打个招呼,但也从未请他们帮过什么忙。
狗儿帮妈妈背回包谷和清洗好的衣服就无事可做了。闲下来的狗儿就不停地想豹子哥,想得心里焦躁不安,也想得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狗儿不善于主动结交朋友,这里也没有跟他年龄上下一般的大男孩。蛮牛对他虽然亲善,但话不多,别人说话时,也多是不时地憨笑一下,平常有什么事了,才跟他说上两句。跟妈妈好像没有多少话可说,孤独和寂寞困扰着狗儿。
在盼望着豹子哥早日回来的孤独寂寞中,狗儿度日如年。
一天晚饭后,王二娃来到狗儿家坐了一会,扯了一会闲谈之后,感觉没有了话题,起身离开时邀狗儿跟他一起去玩。
狗儿征得妈妈同意后,跟王二娃去了水牯家里。
狗儿做梦都没想到山里汉子们是如此的豪放和粗野!
狗儿和王二娃来到水牯家里时,水牯正在灶前生火煮饭,见到狗儿来,急忙起身招呼:“狗儿是我这里的稀客啊,你们两个夜饭就在我这里吃。”狗儿和王二娃都说吃过晚饭了。“反正我也要煮,你们来了,大家就喝口酒,二娃,你去把冉老怪喊来,叫他把酒带来。”水牯一边说,一边搬过凳子用衣袖擦了擦,让狗儿坐。
王二娃出门后,水牯擦洗着茶缸对狗儿说道:“你都来这么久了,啷个不来耍?大家都是兄弟伙,不要见外嘛,朋友不走不亲。”狗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僵着笑脸说:“我不晓得你住在哪里,这阵不是来了吗?”见水牯又是擦凳子,又是洗茶缸,真把他当客人待,狗儿反到拘束起来。
不一会,冉老怪提着酒壶跟王二娃来了,刚进堂屋,冉老怪就拿狗儿开涮:“狗儿今天终于断奶了!来这么久都不出来耍,是在屋里扭着妈妈要奶吃吧?”冉老怪这一说,大家都笑了,狗儿只好跟着笑,脸也有些泛红。
这冉老怪和水牯,狗儿早就认识,狗儿妈嫁到这里来的那天,他们帮蛮牛去接的亲。冉老怪在接亲路上荤话怪话最多,“爹妈给我一丘田”那个“对诗”的故事就是他讲的,水牯就是那个觉得“对诗”太难,说“不相信她捂得住”要强行行事的人。在狗儿以前的印象中,冉老怪是一个油嘴滑舌的骚包,水牯豪爽但粗鲁。现在狗儿觉得水牯粗中有细,对人还蛮好的。这两个人后来也去过狗儿家里,但注意力不在狗儿身上,只是跟狗儿礼节性地打过招呼。
见狗儿有些不好意思,冉老怪更是来劲:“狗儿来我们这里,长得好多了。原来黄皮寡瘦的,现在油光水滑起来了。JJ也长大了吧,梦见姑娘时打过炮吗?”
“你少在那屄酸尿臭的逗得别个不好意思,在外面找点干草给腊肉烧起。”水牯在灶门上方取下一大块腊肉朝冉老怪甩去,再对王二娃说:“到你家去拿点酸盐菜来炒腊肉。”
幸亏水牯解围,狗儿让冉老怪说得有些难堪了。锅里水开了后,水牯泡了一大缸茶端给狗儿:“别不好意思,大家都是男人,混熟了是兄弟伙。”
狗儿心里想:“他们和我也是兄弟伙?冉老怪看上去比蛮牛年龄大,水牯年龄也和蛮牛差不多,我应该是小辈才对。”也许正是这辈份的概念,让狗儿觉得是在长辈们面前,显得拘束了,和豹子哥在一起,狗儿心里就没有这种隔阂。
王二娃拿来了炒腊肉的豆腐干和酸盐菜,也摘了一些青辣,还带了姜蒜等佐料。
冉老怪也给腊肉皮烧好,洗干净了放在刀板上,拿着菜刀在上面左比比右划划,就是不切。
“你在搞些哪样名堂哦?”水牯见冉老怪又在装怪了,忍不住问他。
冉老怪一本正经地说:“这块腊肉一烧一洗,现在里面热噜噜的,我舍不得切,我在看,从哪里插一个洞,先让你拿去用一用,再切了炒来吃。你那佐料放在里面,还多一种味道。”
“你自己想用,就插个洞先用一下吧。二娃,你就别和他争了。腊肉是他烧的洗的,他有功劳,该奖!”水牯笑着说。
“不和他争,我这里烧好了几个海辣,切碎了放在那个洞里,老怪用起来肯定更爽一些。”王二娃在灶堂前拿起烧好的青辣笑着说道。
有酒有肉有客人,汉子们快活得跟过节似的,相互戏谑调笑间,七脚八手一会功夫就做好了饭菜。菜很简单,但很诱人:一大钵渣海辣和豆腐干炒腊肉,一大盆白水煮嫩南瓜,一碗凉拌黄瓜,一碗炒茄子。另外还有一碗用来吃白水南瓜的调料……剁碎的烧青辣和大蒜。
王二娃取来四个碗放在桌上,水牯提来酒壶先客后主地正要给狗儿倒酒,狗儿急忙给碗拿开说道:“我不喝酒。”其实狗儿也不是没喝过酒,蛮牛喝酒时,都要让他喝一些,开始狗儿妈还劝阻,蛮牛有他的理由:“哪有男人不喝酒的?”但狗儿喝不了多少,山里汉子们的海量和劝酒斗酒的疯狂劝也见识过,他是怕被灌醉。
“男人无酒不欢,你又不是小娃儿,嘴上的绒毛都转青了,胯脚的毛也肯定长了一大遍,大男人就莫闪劲。”冉老怪说着怪话劝狗儿。狗儿不知道怎么推辞,拿着碗尴尬地僵持着,心里有些后悔来水牯家了。
“你能喝多少,我给你倒多少,这可以了噻?”听水牯这样说,狗儿才爽快地给碗放到桌上。只倒上小半碗时,狗儿连忙说:“好了,好了!”水牯没勉强狗子,接着给冉老怪倒酒。
冉老怪把手掌朝自己的碗上一盖,看了一眼狗儿那只有小半碗的酒,“恨”着水牯说:“茶斟七分,酒斟十分,这个礼节你都不懂?你这样待客,也不怕得罪人?”
“十分就十分,狗儿,我给你倒满,你能喝好多算好多,尽兴就是了,喝不完算我的!”水牯给狗儿碗里倒满后,再给剩下三个碗全倒满了。
水牯端起酒碗说:“今天是狗儿第一次来我这里作客,这第一碗酒是欢迎小弟的,我们三个干了,狗儿随意。”三人一饮而尽,随后大家忙招呼着狗儿吃菜。
“我们兄弟伙今天多了一个小兄弟,按理说,我们和蛮牛是兄弟伙,狗儿是小辈,辈份论起来,就显得生份了,也不亲热,笑话都不好说。我们各依各教,狗儿也是我们的小兄弟,以后狗儿就叫我们名字,在后面加个‘哥哥’也可以,这碗兄弟酒我们干了!”
狗儿觉得冉老怪说话头头是道,也说得他很受用,像冉老怪这个年龄,叫他叔叔,还不勉强,但叫水牯和王二娃叔叔,让他觉得别扭,狗儿正为怎么称呼他们犯愁。冉老怪好像看出他的心思了,给他解了难题。冲着这一点,他们干酒时,狗儿也喝了一大口。
王二娃的那碗对狗儿祝福酒干过之后,狗儿也很有礼节地端起酒碗说:“我不敢干,我敬三个哥哥!”
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下来,煤油灯下,大家继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已有醉意的狗儿在这豪爽氛围里,不再有一丁点拘束,感觉自己已经融入这伙兄弟中。
微醺的冉老怪拍着狗儿的背说:“小兄弟,你慢慢地就晓得了,我们兄弟伙像一家人一样,像水牯、豹子和我,以前还有蛮牛,都是单个子人,没有亲人了。把兄弟伙就当自己亲人一样,走到哪家吃哪家,衣服裤子都可以打伙穿,就是亲兄弟都还没有这么随便,哪样事都可以帮,哪样事情可以做。”在说最后两句时,冉老怪意味深长地加重和放慢了语气。
冉老怪的话勾起了水牯的苦衷和无奈:“我们这些单个子人,仰起有卵一条,趴起卵都没得一条,又在这个鬼地方里,这辈子只有打光棍的命,当断尾巴(无后代的人)了”水牯说完,重重地叹了口气。
“话也不能不么说,人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过得快活就好。你就是儿孙满堂,辛苦一辈子,死了后还是得个土堆堆。我们这些光棍,除了胯脚那个东西没得放处,过得还是快活。单身汉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没有老婆娃儿的拖累,也少遭些孽,再说,也不是没尝过女人的味道。”冉老怪好像既是在宽慰水牯,又是对大家发感慨。
话题转到了女人身上,三个人可能是想在狗儿面前炫耀,各自吹嘘着从女人那得来的经验。
“那回在镇上剃头,那个洗头妹开始要一百,我那时身上也只有一百,给她了,我饭钱都没得了,就和她讲成五十。我刚一插进去,她一把就给我后面半截抓住不准进了。我问她:‘你搞哪样?’她说:‘你只给五十,就只准进一半’,这个时候,我哪里停得下来?对她说:‘你放了,一百就一百’。”水牯的性经历滑稽搞笑。
醉醺醺的狗儿跟着大家笑着,下面也硬了起来,感觉前端还湿湿的。
“恁个就做完了?”冉老怪问道。“还要啷个嘛?害得我饿起肚子回来,半路上在土里刨了几个红苕吃,脚杆才没打闪闪。”
“你那一百块钱也花得不值哦,我就晓得你只会那个狗刨骚!”冉老怪一副行家里手的口气。
“送个女人给你,你都玩不转。”冉老怪挖苦起水牯来。
“你玩得转,你啷个玩法?”水牯受了贬损,心里不服气:“做这种事,哪个男人不会,还要你教不成?”
“这里面花样多得很,有三十六招七十二式,比如:芭茅翻蔸,岩鹰闪翅,飞蛾爬壁,老汉推车,隔壁取火,说都一时说不完。有次赶场回来,路上遇到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我几逗几诓,就把她弄到手了,钻进包谷林里,翻来覆去把她搞晕过去了。”冉老怪不无得意地说着。
“就你那个样子,我看是‘三百斤的野猪……得一张嘴’,怕是那个妇人把你搞晕过去了还差不多!”水牯认定冉老怪是故弄玄虚的“假老练”,抓住机会反唇相讥。
“人不可貌相,你和二娃的那个东西可能还不如我的,不信我们就比一比。”冉老怪做男人资格受到了轻视,醉意之下,要挽回面子,站起来把手从裤子的尿门里伸了进去。
“比就比”令狗儿感到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三个男人在酒精的作用下,还真从裆里掏出各自那根硬东西来,在朦胧的油灯下,比试着长短粗细,他们就跟比手脚大小一样,毫无羞涩之感。
狗儿靠在板壁上,装作见惯不惊的样子,醉眼迷朦地欣赏着这从未见过的场景,心中有一股莫名的东西在升腾。
“我就说嘛,人不可貌相,还是二娃卵长二分。”冉老怪有先见之明似地说道,明褒王二娃,暗贬水牯……别以为你有一副好身板,那东西就比别人的粗大。
王二娃洋洋得意,还真像得了什么冠军一样。感觉脸上有光的王二娃问着冉老怪:“你说的那些招式,啷个做?芭茅翻蔸,是啷个翻蔸的嘛?”
冉老怪醉眼斜睨着王二娃:“这个吗,‘要得手艺会,就陪师傅睡’,以后慢慢教你。”
水牯接着说:“今晚是月黑头,看不见路。大家都有些醉了,回去不方便,就在这里挤着睡吧,二娃在这里陪师傅睡也可以学学‘手艺’。”
狗儿有些过量了,虽然那一碗酒喝剩小半碗时,水牯代他喝了,但狗儿还是感觉昏昏沉沉头重脚轻,就跟他们一起到了睡房,和衣横躺在床上。
半夜里,狗儿让一张嘴唇上的胡子扎醒了,脑子也先前清醒了一些,顺手摸去,身边是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一只手还从他裤子的尿门处伸了进去,摸着那里面硬梆梆的东西。狗儿这才想起是睡在水牯家里,狗儿把那只手从裤子里拉了出来,翻了一个身,背对这人。迷糊间,狗儿感觉床在抖动,稍远处传来粗重呼吸,狗儿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过一会,身边这人也侧过身子,前胸贴在狗儿背上,下面硬硬的顶到狗儿的股沟。
狗儿一动不动地侧身睡着,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给他搂着,身体越贴越紧,背后下面的坚硬隔着裤子在股沟里摩擦着,狗儿的生理欲望被撩拨起来,心跳加速,呼吸也不再平缓。
狗儿还是竭力掩饰着内心深处的渴望,下体朝前挪了一下,离开了后面那根东西。后面的人知道狗儿醒了,拉着他的手朝后面移去,滑过大腿放到男根上。从浓密的腿毛和硕大的蘑菇头,狗儿知道这人是水牯。
顺着水牯的引导,狗儿在水牯那里摸了两下就抽回手去。水牯轻轻地给狗儿侧着的身子扳平,骑身上去,狗儿本能地给压在上面裸身的水牯抱了一下,双手退到他两肋轻轻推开,水牯翻身下来,侧躺着搂住狗儿。渐渐地,搂住狗儿的那只手向下滑去,摸索着解狗儿的裤带,狗儿把那只不安分的手抓住移开。
狗儿内心挣扎着,身体被欲望啃噬着。心底里渴望着敞开自己与身边水牯赤裸相拥,尽情地享受健壮雄性的男体,但行为上又本能地抗拒着,狗儿也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拒绝渴望的男体。
充满矛盾的抗拒是非常脆弱的,好在水牯没继续纠缠,否则狗儿会立刻土崩瓦解。当水牯的手被狗儿移开后,慢慢地朝王二娃他们那边翻过身去时,狗儿心里还若有所失。
早上醒来,狗儿首先看到的是水牯赤裸的后背,浓密而顺贴的汗毛沿腿而上,在臀部下方往股沟里集中,再顺着股沟而上,成带状地延伸到背脊。抬起头来,只见三具裸男叠股交臂酣然于梦中。狗儿收紧呼吸,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他们,想到自己要是昨晚放开了,现在也在其中。
狗儿感觉一股热流在脐下涌动,失去夜幕的掩隐,羞涩感的增强和窥视的不光彩让狗儿的脸微微发烫。狗儿轻缓地起身下床,瞥着床上的雄性悄然离去。
幽静山寨的蝉鸣显得格咶噪,此起彼落闹麻麻的一片,让狗烦躁不安,心中有一股莫名的躁动。跟蛮牛一起下地收割麦子,也心不在焉。一不留神,割麦的镰刀滑到手上,划出一个小口子。
昨夜和今晨的那一幕幕不时浮现在脑海里,也让狗儿困惑:为什么当时既渴望又要拒绝呢?可能是跟他们不太熟悉,自己没出息,认生害羞;也可能是担心自己对男人的欲望让人发现,要掩藏内心深处的隐秘;还可能是怕他们没羞没臊,口无遮拦地说出去让人耻笑。
“豹子哥跟我睡在一起时,怎么就那么规矩?要是豹子哥能像水牯那样,正是我所期待的,不管他干什么,我都愿意,我都喜欢!”狗儿这样想着,好像若有所悟:水牯搂着他贴上他后背时,他想到睡梦中的豹子哥也这样贴过他。当时想到了豹子哥,也是抗拒肉体诱惑,拒绝水牯肌肤之亲的原因,心底里隐约存在一个叫“节”的东西。
“豹子哥啊豹子哥,你现在在哪里?好久才回来啊!”狗儿一想到豹子哥,心就像被人牵着扯着,眼睛也痴痴地朝着豹子哥离去的路上望着,希望奇迹发生……在那条路上突然出现豹子哥回来的身影。有时心里还会生出一股怨气:“豹子哥啊,你为哪样不让我跟你一起去?”
豹子的这次狩猎虽然收入颇丰,但也是他狩猎最辛苦的一次。夏季本来不是外出远处狩猎的季节,以前在夏季,豹子就从未出过远门狩猎。蚊虫叮咬自不必说,突降暴雨不仅是淋湿衣裤,更主要的是野兽的脚印被暴雨冲刷之后,难以辨别新鲜和陈旧,给安套带来困难。高温烈日,套到的猎物,活的容易死,死的容易臭,一旦猎获,不管多少,必须及时送到城镇卖掉。
豹子就这样往返于城镇和深山之间,好几次都是披星戴月肩负猎物行走在去城镇的山路上。有时到了城镇天还没亮,好在县城和镇上都有一两家野味餐馆的老板,在买卖中跟豹子混熟了,叫开门来,主人看着豹子先诧异,后是叹息……要钱不要命了!
除了狩猎由闲散乐趣型转变为艰辛劳作型而外,豹子另一个变化就是:以前发现野鸡野兔这些小动物,只是顺便捕上,除了果腹,便是送人,从不拿到市场上销售,他要维护猎人的面子,怕被人耻笑……沦落到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了!而这次狩猎得到的野鸡野兔稍多一点,他还是放下猎人的架子卖成了钱。
狗儿的出现,让豹子有了实实在在的生活目标。艰苦的劳作并没让豹子心里感觉苦,而是充满了甜蜜,是充实而欢乐地朝着美好的憧憬奔去。
狗儿有了这三个新朋友,不再感到寂寞和孤独,三人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待,也让狗儿对他们也产生了亲切感。习惯了冉老怪的荤玩笑,不但不觉得尴尬,反而感到有趣,言谈间还近墨者黑地多了一些粗野;水牯对狗儿依然呵护有加,好像狗儿真是他亲弟弟一样,仿佛那晚的事原本就没发生过,狗儿由此对他生出一些敬意,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一些豪爽的气质。
狗儿虽然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但再也不敢跟他们一起或其中某人睡觉,他怕赤身裸体地睡在一起后,经受不了那种诱惑,回绝挽留的理由很简单:“我晚上不回家,妈妈担心得很!”
豹子满载而归,回到山寨时已是深夜。他恨不得马上见到狗儿,但又怕深夜里惊动蛮牛一家,再说全身也太脏了一点,还带有猎物的膻气和异味。豹子看着黑灯瞎火的蛮牛家房子,犹豫了一下,还是往自己家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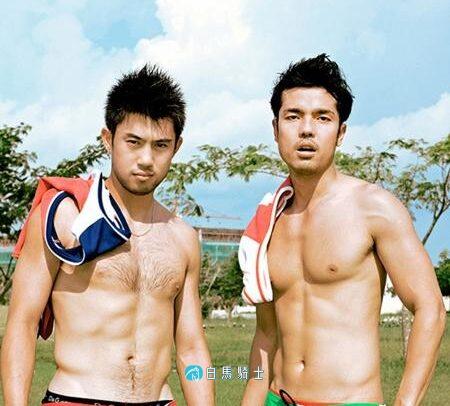







![豆瓣9.1超感人瑞士剧《戴上手套擦泪》百度网盘迅雷下载[完结]-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030615424334.jpg)
![[谢梓秋]正装白衬衣诱惑型男写真BodyStyle 20[86p]-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8/1629707018.jpeg)
![巨根筋肉BL男主角H漫设定原画插画壁纸[90p]-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1/04d7f833c0f994faf4c4aa99ed8b0877.jpg)
![[BLUEMEN]蓝男色NO.200 超人气体育男神允硕全见版-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6077725.jpg)
![[VIRILE]男蓝色摄影体育系天菜男神允硕双人写真-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2/05/1651770640.jpeg)

![[1083张]惊人超大24cm,美混血帅哥网红李亚斯私照流出-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1/1632828731-092811321143.jpg)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