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梦(二)
一碗米粉被搅成了米糊,黏巴巴地粘在筷子上,唐子豪把筷子一搁,脸黑乎乎道:“我不吃了。”
“你敢!塞也给我塞下去!”
叫嚷的是唐爸。
父爱如山,此时却像山崩地裂,馀音穿云裂石而来,喷了唐子豪一脸,他若无其事地摆动著两条伶仃细腿,默默地把碗端进了里屋。
他身高堪堪到达母亲的肩膀,要想看清后者的脸,得把头上仰百二十度,这动作他做得多了,倒不觉得脖子有多难受。
母亲摇摇头,无可奈何:“别管他,自己做作业去。”
“不了,我约了同学。”
母亲脸色一变,食指竖在嘴唇前,示意他闭嘴。
“你又牵什么梁子?小心你爸爸知道。”
“不用那幺小心,”唐爸声音雄浑,“我早就知道了。”
他自顾自走进来,双手成拳,此时有种虎毒食子的冲动。
唐子豪把身子一侧,躲到了母亲身后。
“别打我。”
“谁要打你?打得半残不死的,不是浪费钱,折磨我自己吗?唐子豪,你给我过来。”
唐子豪摇头,片刻之后,似乎觉得有所依靠,心里莫名有了底气,试探道:“我要去讨债,你别拦我。”
“那你就去啊。”唐爸给他让出一条路,“去。”
欲擒故纵?唐子豪心道。
第二天那天下午,老街上跳动著泥巴颜色的水花,一朵朵,阴差阳错地打在了他的裤腿上。
他因此只得把裤脚卷到了膝盖,活像一个要下田插秧的。雨伞杆子在他手里摇摇晃晃,仿佛天雷一震就要掉到地上去打滚了。
一家小卖部的排门打开了一扇,他把伞一收,趁著雨滴还没来得及溅落,一闪身就去了。
此时正是初秋,又来了这么一场雨,温度被降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度。屋子里是另一片小天地。
零食架旁边排著两三张麻将桌,有人在桌子下面放了个暖脚器,手则在一团乱哄哄的麻将里乱穿。
唐子豪东打西望,才看见了这次寻找的目标,一脸正气地走了过去,英勇就义一般。
那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
“大娘。”
“哟,唐子豪,”老妇人一惊,“放学了?”
“放了。”
“看这咋衣服都湿了,伞放下,过来烤烤火,湿衣服脱了吧,我去给你找件杨允的衣服穿上。”
唐子豪闻言一手抚上了自己的衣裳,才发现外套已经湿了半透了。
“不了,杨允呢?我找他。”
“他呀?去玩了。”
“这么大的雨他去哪里玩?”
“兴许是哪个小孩的家里玩游戏了,你有事?”大娘热情地把他的东西接过来,给他打了一盆洗脚的热水。
唐子豪的话哽在喉咙里,由于不可抗力被卡在一个尴尬的地方,下不去出不来。
杨允是大娘的孙子,算起来唐子豪还是他的长辈。
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一年级起,唐子豪就被迫这个娇生惯养的形影不离,一起上下学。
老街上有他们的产业和新房,碰上赶集那天,杨允可以有不走路回家的权力,而是一身轻松地就在这里,日常和他的街坊邻居小朋友们去后街捡小鞭炮玩。
而唐子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穿行于崇山越岭,鞋子磨得很快。
他那时候想:大概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也不过如此了。
杨允的撒娇劲不讨人喜,却是跟他黏得“如胶似漆”。杨允小时候手便不干不净的,零花钱有一半都是在家里的柜子里摸来的。
他为了让唐子豪保住秘密,还特意每次给了他封口费,或是给他买糖,或是送他自己的积木,种种手段,不一而足。
唐子豪向来不喜和钱计较,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另一方面,打小报告也不是他的专长。
果然这次,他还是没能拗得过自己的性子,咬咬牙,狠下心走了。
大娘一边嘱咐他慢点,当心摔坏,而后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脸色一黑,转身过去拨通了唐爸的电话。
回去之后,唐子豪被胖揍了一顿。
唐爸幽默风趣地卖弄著他狗屁不通地脏话,一边用黄金棍抽他屁股一边唾沫横飞:“我|日|你妈!我|日|你妈!”
唐妈在一旁默不作声,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她已经把女子三从四德的传统美德贯彻得彻彻底底。
“我才日|你妈!”唐子豪从牙缝里憋出一句。
这话也不是为了侮|辱谁,唐子豪气急了,又不懂那不过几笔的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只当解气,一股脑地抖了出来。
唐爸一震,抄了一把菜刀。
饶是唐妈再镇定自若,也不能不管不问了,她上前握住他的手,有气无力地训斥:“你做什么?”
“丑女人!你还拦我!放了不放?!”
“不放,虎毒不食子,你这是要遗恨终生!”
“给老子滚!”唐爸朝唐妈腹部一踹,后者一下滚到了墙角,抱著肚子苦叫不迭。
唐子豪上一秒还趴在凳子上,听见身后人挥刀的风声后,一个激灵滚到了地上。
那把菜刀嵌在了凳子里,刀片还震颤了几下。
唐子豪被惊出一身冷汗。
唐爸丢了刀柄,一掌把唐子豪拍到了地上,脸和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
“我问你,你是不是去找杨允了?”
唐子豪吞了一口半酸不苦的唾沫,委屈道:“不是你让我去的么?”
“老子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吃屎你要去么?”
“我……”
“别给我装可怜,你和你妈都是一个德行!有其母必有其子,你们果然是串通好的。”
唐妈幽幽传来一句:“串通了什么?”
“串通来索命!黑白无常!你们就是黑白无常!”他说著把矛头指向了唐妈。
“丑女人!我不给你资格,你没有发言权!你就是一条贱命,只配给人家擦鞋的贱命!好啊,你不是喜欢跳舞吗?很好,我剁了你的脚,看你怎么飞得起来!?”
唐子豪牙齿一震,舌头被咬得生疼。
往往是这种千钧一发之际,救命星到了。
矮矮胖胖的闫二婶迈著蹒跚的步子姗姗而来,对著发疯的唐爸就是一阵淋头狗血。
唐子豪占时把心安了,落荒而逃,一瘸一拐地揉著著火的屁股到了院子里。
老大哥用一把精致的水果刀雕刻著一管竹子,看她来了,冷漠得连眼神都不屑给一个。
唐子豪有意无意地走近了,对著他不断变换方位的手的刀子出神。
老大唐华英乐于将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为了消磨他的斗志,特意找了一句十分不入耳的:“唐子豪,过了今天,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了。”
“我知道,我爸妈他们吵得厉害,估计都想去死,我不期待谁要养我。”
“你就不害怕?”
“害怕什么?”
唐华英动作一停,正襟危坐地卖弄他年长之人的“博学”:“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流浪者没有权利忧伤,因而他们只是泄愤的工具罢了。”
唐子豪十脸懵逼:“???”
“我是说,你以后就算跟了哪一个,也不会有好下场。你爸嘛,成天喝酒,说不定哪天不悦酒瓶子就砸你头上了。家里有一只老虎,时刻刻需要提防的。至于你妈嘛……咳咳。”
唐子豪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你咳嗽什么?”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你是天生痴呆还是被迫装傻?你爸妈之间早就有隔阂,看不出来么?”
“看出来又怎么样?”
“你看得肤浅。”唐华英附在唐子豪的耳边说了不知一句什么,让后者从耳根一直红到了眼睑。
唐子豪:“不可能!你骗我!”
“傻弟弟,血浓于水,我何必以疏离间?”
“可是血浓于水,我也相信我妈不是那样的人。”
“眼见为实,你没看到就别瞎说,免得日后被打脸。你跟了你妈,说不定你那个后爸也要折腾你,省省心,干脆谁也不跟,自己去死算了。”唐华英收了这个话题的尾,又专注地雕刻他的竹子。
“唐子豪,你迷信不?”
“不。”
“那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他把被削得尖锐的竹子举起来,“我教你诛心。”
“我跟你说了我不信这些。”
“那不行,你总得让我说。”
“……”
“这个竹子你拿去,搞点鸡血抹在这尖上,月圆之夜的时候放到山下的小河沟里冲一晚上,对著它,保持清醒。第二天取出来,再抹鸡血,用它扎人,默念一遍你的愿望,那人就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什么鬼?这是哪里读来的巫邪术?”
“自创的。”唐华英笑出了两瓣门牙,“只此一家,别无仅有。”
他继续解释:“第一次抹鸡血,是用以安慰河里的神灵,第二次抹鸡血,是为了避免异源血侵染圣物。竹子是本大师开过光的,百用百灵。”
“……你不会让我拿这个去扎我妈?”
“那又怎么样?又不会死。”
“日|你个鬼,自己玩去吧,别烦老子了。”唐子豪不屑一顾,“我妈肤浅惯了,也封建惯了,我才不信她能干出这种……那种……叫什么来著?”
唐华英急急忙忙接了话茬,胸有成竹道:“有辱门风。”
THE END







![[R18]恶魔和青年The devil and teen S-13四格漫画-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0/03/cf84ebd24a3a131a067fe6bf4c688dac.jpe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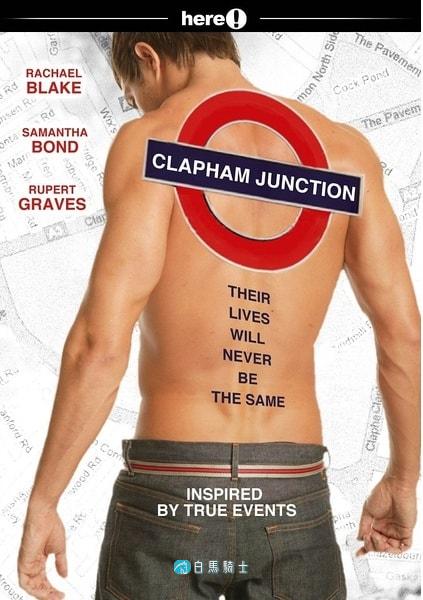


![[BL游戏][PC]合租大街正式版+通关存档-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5804084.jpeg)

![[BLUEMEN]蓝男色NO.200 超人气体育男神允硕全见版-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6077725.jpg)
![[1083张]惊人超大24cm,美混血帅哥网红李亚斯私照流出-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1/1632828731-092811321143.jpg)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