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张垒走了,张垒说他走得很坦然,很轻松,也很开心。
号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大家都这么静静的坐着,抱着膝盖静静地坐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张垒走的那天早上,看守所吃的是小米粥。对,是小米粥。
5月6日,洪流来看我,顺便带来了几本书。洪流告诉我,伯母今天回来,淑华接飞机去了,至于案子的事,现在仍没多大进展,本来汪勇、和涛他们都来了,可是人家不让进,现在他们都在接见室外面等着呢!
我看着洪流,一直没能插上嘴,只有陪着笑。
“哟!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洪流发急了:“我们都替你难过死了!笑?还笑!”
“不明白了吧?”我告诉洪流,这其中的奥妙是没有住过监狱的人永远也无法体会到的。“唉!”我叹了口气:“洪流啊洪流,人生苦短,好梦难圆,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感激的心态来面对自己所经历和承受的一切,有一首歌唱的很好,‘眉间放一字宽,看一翻人世变幻’。”我咳了两声,清清嗓子:“要不,我唱给你听?”
“打住打住!”洪流右食指顶着左手心,他拧着眉头看着我,挺惊讶:“你——不会是神经了吧?”
“我正常的很呢!”我歪着头趴在桌子上拨弄着一页页翻过的书角喃喃着,我告诉洪流,以前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有个叫但丁的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本来就是一座炼狱,如果不想在炼狱里死亡,就一定要升华”。我这是第二次住进监狱,亲身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尤其是在张垒上路那天早上,我突然之间豁然开朗,是啊!财富的拥有、名利的双收、权势的驾驭、美色的诱惑,这一切的一切对于生命的结束来说,真的只是过眼云烟,如梦似幻,不值一提……
“你变了!”洪流摇摇头说他现在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仍然觉得财富是最主要的,要不然……”话说一半,洪流一下子沉住了脸,他停住了口,面无表情。
“有什么就说呗!”
“要不然小涵也不会走。”洪流的声音很小:“小涵辞职了。”
“哦!”我的心猛地一沉。
“她去南方了!”洪流悻悻的,有些激动:“她已经走了!”
“是吗?”
“你真的没话可说?”洪流板着脸瞪着我问。
“没什么可说的。”
“你这人真是无情无意!”洪流涨红了脸腾地站了起来,险些掀倒身边的桌椅:“我以为你会难过,最少也关心一下,可你——”他斜着脸,朝我射来束束鄙夷的目光:“我真替小涵感到不值。”
银河传媒每天有员工进就有员工出,我不知道小涵另谋高就的离去跟洪流有什么关系,我更不明白洪流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是的,我想不通。至到洪流那副苦大仇深的怒容还有那双红肿的醋浪淘天的冷眼消失在我面前很久很久,我仍是不能理解,最终,还是随即而来的和涛替我解开了这其中的谜。
和涛告诉我,在我还没来石家庄前,洪流就跟小涵在谈朋友了,是我的到来打碎了洪流的美梦,“城哥,这不怪你。”和涛安慰我:“是她自作多情,不关你的事。”
哦!是我的错!我总算明白了,全是我的错!我喃喃自语往回走,洪流那句流着泪的问话一直响在我耳边,“夜倾城,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为什么会出现,小涵走了,我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
我流泪了,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自由。
回到号里,放好书,洗个脸,不到十分钟时间,管教又通知我接见。
是谁?伯母吗?伯母找到人捞我来了?我兴奋地飞奔至接见室,来人却令我大吃一惊,是……是是是我的老同学——温——秋——生!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揉眼,我猛跑一步,抱住了他,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
“老同学,我们又见面了!”秋生在拍我的后肩,他叫我别难过。
秋生还是那样瘦,仍是那样的文质彬彬,不同的是,如今的他戴了一副金边眼镜,这一身黑色的西装包裹的他更加成熟、英武、俊朗。我们就这样互相看着,激动得……激动得竟然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走!”
“走?”我指指身边的铁门电网:“老兄,你以为这是旅馆?”
“我不骗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我在这里等你。”他把双手搭在腹部,站的很仪态,说的极认真。秋生告诉我,这次事故调查清楚了,警方认定的结果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肇事者也已经被抓进来了:“这一切都是我表哥的功劳,他在给你办手续。”
“你表哥?谁?”
“等会你就知道了。”秋生把我往外推:“好了,快点去收拾东西吧!”
回到号子里,拿好衣服揣上书,跟众位难兄难弟响亮地说了声后会无期,然后我就跟着秋生迈出了威严的铁门。
今儿,阳光灿烂,凉风习习,喜鹊在头顶飞来飞去,难怪有贵人驾到救我夜倾城呢!
“迪迪……”秋生一扬手按响了摇控:“这边!”秋生打开了车门,请吧!“
宝马!我看看秋生,又看看眼前的车,我问秋生这辆车的主人是谁。秋生一猫腰钻进来坐在后排临位告诉我,这车是他表哥的。
哦!很显然,车上缺位司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等他表哥。
”喏——来了。“秋生把手伸向了窗外。他指着对面一个匆匆跑来戴着大墨镜的男人告诉我,来人就是他表哥。
”好熟悉的影子。“我嘟囔了一句。
”那当然!“秋生看了我一眼,很自豪:“石家庄有几个人不认识他的?”
那身影走近,开门,上车,落座,取下墨镜。天哪!是……是李真达!我顿时手无足措,浑身爬满虫子般难受。
“秋生,去哪儿啊!”李真达扭过头看了我一眼,露出难得的一笑。
“燕风楼。”秋生拍打着我的衣服说要为我洗去这一身霉气。
我告诉秋生还是下次吧!我想先回青园街,伯母他们一定都等急了,“要不然,我先打的回去,改天我再专门摆晏向你们道谢。”
“你丈母娘那里吧?我知道!”李真达一踩油门,车就飞了起来。
“也好,不过我得送你到楼下。”秋生想了一下,他抽抽鼻子自我解嘲似的说了一句:“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原来,当年自6·4退学后,秋生就投奔了李真达,几经风雨,秋生说他如今供职于河北外贸局,担任省进出口公司的业务经理一职,发展得还不错。“老同学,其实你来石家庄的第一天,我就听人说了,我也曾再三决定约你出来以叙同窗之情,但又怕触动埋在心底痛彻心脾的一幕。”秋生说的黯然神伤:“阿城,如果不是你这次入狱,我想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见面。”
我点点头,很认真的听着。秋生说当他知道我从婚礼上被抓走的时候,他就如同被电击了一般,脑袋轰的一声响,面色煞白,半天回不过神来。秋生抓紧了我的手苦笑着,不吭声了。
我握紧秋生的手,心中只剩下了感激,我摸摸玻璃,摸摸座椅,然后抬着P股晃动两下。秋生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这是我第一次座宝马:“其实宝马、奔驰呀也没有什么区别,买的人不一样,坐的人心情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才有了好坏之分。”
“行啊你,是在拐着弯拍我马屁吧?”后视镜里,李真达笑的很灿烂,他猛地一踩刹车:“到了。”
“那我就不上去了。”秋生递给我一张名片:“以后常联系。”
“秋生,真的是谢谢你!”目送着宝马离开我的视线,我终于说出了憋在心底的一句话。秋生,你知道吗?我也常回到那个使我们都可以听到皮肤皲裂的日子,夜里,梦中,每当凄历哀号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一次次将我惊醒的时候,我也常拖着腮帮子,用一种可怜巴巴的目光看着身后的影子,收拾着自己的情绪,魂不守舍,这种感觉这种无奈这种痛这种怨是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6·4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刘妈买菜去了。伯父还没有回来,伯母在家。
“回来了!”她像早算准了似的。
“嗯!”我把行李放在地上。看见她,张垒的话立即如波涛翻滚般一浪高过一浪在我耳边回响。
“李真达总算务实了一回,快坐下歇歇。”她转身去倒咖啡。
哦!原来伯母早就听到了口风。可是,可是她真如张垒所说的那样可恶吗?我傻傻愣了好一会,瞟窃她一眼,我的脸莫名其妙一阵辣红,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胸口“砰砰砰”直跳。她……她连背影都那么超凡脱俗、与众不同,自信的让人不容置疑,我……我还能怀疑什么呢?
“愣着干嘛?不烫,快喝吧!”拨拉着茶几上的一个个纸包,她颔首而笑,像是在自言自语:“你回来,我也该松口气了。”她拆开纸包。我看到包在纸里的全是花花绿绿的药丸。
我的目光就这样游离在她的脸上,而她像是懵然不觉。我将咖啡一口灌下,小心翼翼地问她是不是病了。
“胸闷。”她把药倒在手心,一扬手扣在嘴里,和渗着一口水,伸长了脖子,我清楚地听到了“咕咚”一声响。
“伯母,怎么不见淑华?”
“去派出所了,快回来了。”她捶着胸口咳了起来:“这两天够她焦头的了,先是你被抓,接着就是她的秘书,咦——你说,也怪了,一个小秘书竟然自作聪明胆大到善自篡改施工图。”
“悠哲?伯母你说悠哲是肇事者?”
“那当然,最可恶的是他竟敢冒用你的签名。现在好了,真像大白,死了六个人,他不下地狱谁下?”她伸了伸腰叹道:“这也给我敲了个警钟,用人一定要慎之再慎。”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失去了知觉,接下来就是从头到脚渗透着一种彻骨的凉。天哪!施工图、数据、签名,我……我……我拨腿就往外面跑。
“你要去哪儿?”伯母在身后大声质问。
“我要去跟警官说请楚,数据是我改的,名字是我让悠哲签的,这一切跟悠哲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颤抖的历害:“我……我才是罪愧祸首!”
拉开门,淑华正巧拿着钥匙准备开门,她惊恐地看着我——她已经闻到了火药味。
“不准去!”伯母历声呵斥:“法官只讲证据,你的证言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不相信我也得去。”我被憋的吭哧吭哧喘着粗气:“这是事实。”我推开淑华就往外跑。
“这不是一个讲实事的年代。”伯母突然之间面目狰狞、凶神恶煞朝淑华一声大吼:“站着干嘛!还不拉他进来。”
“你们这是干嘛?阿城,你要去哪?”淑华猛地把我推进房内,一顺手她反锁着了门并把在门口。
“他要去送死!”伯母掐着腰,转过身,冷眼逼人。
淑华吓的脸色发青,忙问我怎么回事。我把更改数据、签名的原委一一道给她听:“这下,你们都明白了吧?你说我怎么办?做人不能这么自私!”
“你要是再进去可就真出不来了,你出不来了我怎么办?”淑华咬紧了嘴唇,合紧的双眼最终还是没能关住流出的两行清泪。
入狱!坐牢!失去自由!天哪!那种滋味……那种滋味……我……我……顿时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胸口一阵阵翻味,想吐,难受,随之而来的是我的双脚,我的双脚怎么样也迈不出一步了……
房内,空气窒息得可以让人飞起来,我瘫软着身子搂紧了淑华。搂紧了她后,忽然胸口又是一股股翻江倒海般的难受。我想推开淑华,淑华却抱得我更紧了,她在不停在流着泪,大哭着不肯松手。她捧着我的脸,鼻尖对着我的鼻尖。她长长的睫毛戳着我的眼敛。从她那双明亮的随时可以将我灼伤的眼里涌出的滚烫热泪顺着我的脸滑到了嘴边。咸,好咸,还有点苦!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热,真的很热,全身像被烫熟了似的。房内除了淑华的抽泣,还有的就是做为伯母做为梅总做为我未来丈母娘的声音。
她说:“慈不带兵,仁不经商。”
她说:“丰富的情感是商战里致死的命门。”
她说:“在明争暗斗的商场里绝不容许儿女情长。”
她还在说,还要说,我求她别再说下去了。我要淑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好吗?我很难受,这里太闷,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
推开淑华,我打开门。一股凉风吹了进来。
“去哪儿?”伯母扭过头,语气缓和了许多。
我告诉她我要回家,我要睡觉,我累了。我告诉淑华:“你可以留在这里,这里是你的家,我要回卓达花园,我要回去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我的桃树然后看看桃子长大了没有,对了,新闻上报道过了,今晚有流星雨,百年不遇的特大流星雨……”我喃喃着自言自语往外走。
出了门,抬起脚,下了楼梯,一阶,二阶,三阶……我一直数到了楼底下。
背后传来一阵急急的“咯噔”“咯噔”皮鞋声,我知道,一定是淑华。
淑华说她也要回去,淑华说她要回去看看我们的别墅我们的荷兰猪还有我们的桃花树,家,哪里是家呀,“你到哪我就到哪,你在哪哪才是我家。”
乳月当空,午夜了吧?我仍坐在楼顶天台的水泥地板上,淑华双手交叉抱着膝盖靠着我的肩膀。一整晚了,我们谁都一动也没动,我们在看天。
远处,一条条水泥路静静地铺躺着,默默地延伸到原野的尽头,笔直的笔直的足以能使人闭上眼就能走到天上去。纯净的夜幕在这寂莫中点缀着一抹抹幽黑,到处是神一样的宁静,似乎一伸手就能从脸上抓下一把冷静来。
“快看,流星雨!”淑华拍着手,眉飞色舞。
头顶,一颗流星瞬间“嗖”地划过,忽而不见,紧接着又一颗,又是一颗……
流星雨,好美的流星雨……
那种绝尘之境,真是用文字难以传达!
淑华双手抱拳顶着下巴,她要我赶快闭上眼,许个愿,因为她听人家说这时候许愿上帝能听见,也最容易实现。
抬头三尺有神灵,对,许个愿吧!我夜倾城希望这世上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流星雨。
也包括你,青云。
淑华如影子般陪了我72个小时,在确认我不会做出什么傻事之后放心去月光了。
我能做出什么傻事儿来?天大的事儿睡一觉,第二天醒来,我都会忘掉,全忘掉。这是我对每一个关心我的人所讲的话。
“真的吗?”他们都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瞄得我像是个一屁俩谎的人。
“真的!”我坚定的说出这俩字足以在水泥地板上砸出仨坑。
“你就别骗自己了。”伯母把我叫进办公室。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裱好的白纸、一瓶墨水还有一支毛笔。
伯母的话极具杀伤力,平平淡淡的慢慢悠悠的就戳穿堆在我脸上的洒脱。她挽起袖子拿起笔叫我帮她把纸铺平。
按照她的吩咐,我很快铺平了纸。她挽起衣袖,拿着毛笔,沾饱了墨汁,拧紧了眉头,深吸一口气,然后如水银泄地般飞快写下“宇宙是个友好的地方吗”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未了,她拍拍手优雅地捋捋头发问我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摇摇头。不过我告诉她,我知道这句话好像是爱因斯坦说过的。
“嗯!”她满意地点点头正要说话,有人敲门。
是和涛来了。跟在和涛身边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大汉。这大汉一进门先是低头哈腰,然后就是对着伯母刚写好的几个字大吹大擂。
东北人。他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我不是一个以外表的美丑来决定自己情绪的人,但我见了这人,心里总觉得好难受,不仅仅是我看到了他那张瘦瘦的猢狲脸,最恶心的是他那对与时下审美观极不协调的耸拉下来的肉眼泡。我凑到和涛耳边小声质问他从哪带来个怪物,和涛“吃吃吃”笑着告诉我来人是青东高尔夫球场的顾总。
伯母也真是好脾气。她散漫地斜躺在座椅上,打开抽届,拿出准备好的一张支票问顾总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一切都办妥了。”顾总毕恭毕敬用两张绿色信用卡样的东西换回了伯母手中那张支票。只见他很快将支票揣进怀里,怕飞了似的还拍了拍口袋,然后千恩万谢地在伯母轻轻的一摆手中后退着从外面关了房门。







![[同影]《爱你,西蒙 Love, Simon》2018美国720P1080P英语中字 迅雷下载-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18/08/d3afc5eb1f2a42231e8b241ba9df1ec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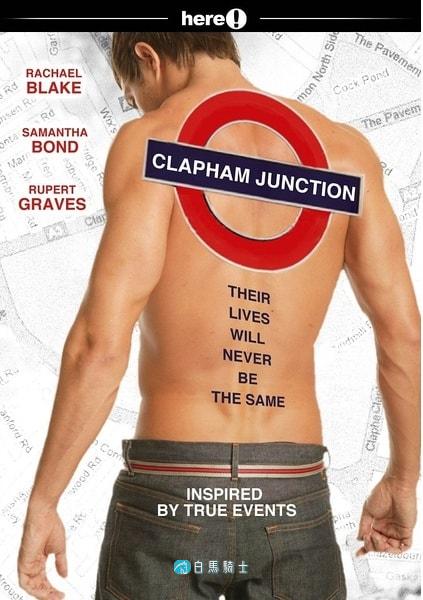
![[BL手机游戏][R18]帅哥公寓管理员v2021安卓英文完美破解版-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5564135-e1615535363561.jpg)
![泰国腐剧《唐人街探爱/我的小奶狗》高清百度云网盘下载[完结]-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9/1632661359-092613023992.jpg)
![[Kissman Photography] 大包超优质体育生集体狂欢118p全见版下载-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4/1619534479.jpg)

![[BLUEMEN]蓝男色NO.200 超人气体育男神允硕全见版-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6077725.jpg)
![[1083张]惊人超大24cm,美混血帅哥网红李亚斯私照流出-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1/1632828731-092811321143.jpg)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