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石家庄,先去拜见了伯父,不,应该叫爸,淑华说了以后不能再叫伯父伯母,要跟着她的口喊爸妈。于是,我朝伯父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只用了一声“爸”就换来一千大元的“利事”。
吃过午饭,本打算回卓达洗澡后好好补睡一觉,可是伯父变戏法似的从卧室里提出山般一堆礼品,要我们赶紧去跟汪律师拜年,“结婚头一年叫拜新年,这些繁文缛节是不能被简化的。”
伯母还没有回来。伯父在装傻。刘妈跟我对迷糊。汪律师好像也在刻意回避这个话题。我套问汪律师伯母对我年前所做的“暖春万花艳之石家庄系列形象短片”都提出了哪些不足之处。
“你是银河传媒的接班人,你应该召集公司高层会议协商而不是等梅总一个人的意见。”汪律师和淑华正在翻看我们在婚礼上的留影,始终没抬头。
见问不出个结果,我拿出老妈给抗天做的虎头鞋跟着抗天进了他的房间。抗天的房内,除了一套半新的组合柜外唯一称得上风景的就是靠近阳台放的盆景了。种的是两株粗壮矮小缠着彩带的桃树苗。抗天说这是他们离开蒲坼的时候从天怡带过来的,“除了抗天外妈妈最爱的就是它们了,夜叔叔,你看它们还有名字呢!”抗天扯开树腰上的彩带给我看:“这颗叫风飞,那颗小的叫顺扬。”
风飞、顺扬,风飞、顺扬,风飞、顺扬……这四个字不停在我的大脑里旋转着。我很清楚的知道这名字一定是青云给起的,我的孩子的名字,我和路青云的孩子的名字……我无力地闭上眼,任泪水在心底打转……
“夜叔叔,你来是不是要取回你和任阿姨的荷兰猪。”抗天蹶着小P股爬到床下拉出小木屋放到被子上,他把小手伸进木屋,一个个揪出小家伙,他托着长音歪戴着帽子看着我笑:“这只——是妈妈,这只——是夜叔叔,这只——”
“还有?”
“这只——是抗天。”抗天从小木屋里掏出只有麻雀大的一只荷兰猪:“我叫航叔叔买给我的,有了爸爸有了妈妈再有个小宝宝,妈妈说这才叫‘幸福’。”他指着小木屋上面的俩个字得意地说。
“你喜欢它们吗?”
“当然喜欢,夜叔叔,你看它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多开心哪!如果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我也会很开心,妈妈也会很开心。”抗天爬到床上用脑门儿顶着三只毛茸茸的肉球玩了一会儿又把两只大的放回了木屋:“你回来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还给你吧!”他把木屋抱在怀里走到我面前。
“既然你喜欢,那我就送给你。”
“真的!”他高兴地跳了起来:“这下小猪猪就不用跟爸爸妈妈分开了。”他接过小木屋,很高兴。忽地,他又垂下了眼,转身递给了我:“可是你也喜欢,任阿姨也喜欢,妈妈说了夜叔叔来取荷兰猪的时候叫我不要捣乱,妈妈还说抗天是男子汉是大丈夫,大丈夫是不夺人所爱的。”
我抱起抗天放在我腿上,我把木屋郑重地塞到他怀里:“抗天,我和你任阿姨都没有时间照顾它们,是我们真心实意要送给你做新年礼物的,妈妈那里我会跟她解释,哦——对了,妈妈呢?”
“舅舅一大早送她去航叔叔那儿了,都怪它——”抗天指着那只比较大点的荷兰猪数落着。
“它?它怎么了?”
“它咬坏了妈妈的信,你看。”他爬到大床上掀开枕头拿给我一个信封:“妈妈还没看呢!”
哦!的确是咬坏的,已经残缺不堪。这荷兰猪就这样,见什么都要啃几下,我房内的书早被它们糟蹋好几本了。我告诉抗天以后可得及时给它们喂食,这家伙饿急了石头都要来两口。
我放下信封,感觉有点不对头马上又重新捡了起来。这不是伯母的笔迹吗?从北京市朝阳区寄来的,朝阳什么地方?下面己被荷兰猪咬掉,邮戳上的日期是最近几天的。我摸摸信封,空的。我愣在了那里。
伯母有信儿了?伯父、刘妈、汪律师他们知道吗?
他们一定知道!那为什么要瞒着我和淑华?难道真出什么事了吗?我问抗天这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抗天只顾拿着一个什么东西逗它们玩:“前几天。”他扭过头叫我:“夜叔叔,你快过来跟我一起玩,你看,它们可喜欢钻圈圈了。”见我没动静,抗天过来拉我的手:“夜叔叔,你就陪我玩吧。”
“抗天,你这是什么?谁给你的?”我一把抓住他拿在手里逗荷兰猪来回钻的一个圈圈——玉手镯。
“我不知道,在妈妈的箱子里找到的,你来陪我玩吧。”抗天嘟着嘴不高兴了。
“那你赶快把这小圈圈放回箱子里去,妈妈看见了会不高兴的。”我脱了鞋跟他上了床,抗天立马偎坐到我怀里:“夜叔叔,还是你抱抱我吧!”
我流泪了,是心泪……
出了汪家的门,我牵着淑华的手,用指尖轻轻探了探她的手腕——老妈送给她的玉手镯还好好戴着呢!
这,这可就真是奇怪了!青云怎么也有一个?我绝不会看错,抗天刚才拿在手里玩的那只手镯跟淑华这只一模一样,淑华这只还是几年前在蒲坼的时候老妈送给她的,平时淑华没舍得戴,只有这次回河南结婚她才拿出来佩戴至今,那青云这只——?
“你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这手镯应该都是一对一对的吧?”
“不知道,反正姨娘的是一对。”
“那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妈送你这个的时候有没有提起另一只镯子?”
“没有。”淑华很果断地否认:“我记得当时婆婆只是说送给我做见面礼,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没事儿,随口问问而己。”
从跨入年后通讯业的发展势头来看,秋生当初执意要开一家手机店无疑是明智之举。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第一批进货己基本销售一空。加之三星、西门子、诺基亚等等一些外国公司看准了中国人的钱包蜂拥而至,这时的手机无论从体积重量还是从功能款式方面让顾客都有了更大的挑选余地,而飞虹手机行的柜台上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秋生合理地利用着手头上的便利还有无所不能的表哥李真达,相信今年一定能赚得脑满肠肥。
那——是一个财富快速增张的年代。
淑华显然已经厌倦了月光俱乐部声色犬马的夜生活,她又聘请了一位大堂经理和一位公关经理主管俱乐部的大小一切事务,而她每天的工作除了查查帐就是跑跑银行,过多的时间她都愿意呆在我的办公室里,给我倒倒水捶捶背,然后笑上一两句。她不是真开心,我知道!怕她感觉无聊我提出“现在卖手机这么赚钱,要不然趁早咱也开一家?”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呀!老公,给人家秋生留口饭吃吧!”
“说的也是。”
伯母到现在也没个信儿。洪流他们一点儿都不着急;汪勇说梅总一向都是这样;和涛说梅总外出从来不带手机也很少打电话回公司;伯父说急什么到回来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刘妈总是无言;汪律师也只和我谈公事;阿航呢?阿航总是忙,忙他的装修生意忙他和路青云的感情。其实,其实我也很忙。
我一直觉得最少青云知道伯母的行踪,青云知道了,阿航也一定会知道,我打电话征问阿航伯母从北京来的信,阿航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我提出一起吃个晚饭,他说正在工地,没空。那我就只有不请自到了。
4月16日下午,汪律师要我在一张两百万的支票上签了字。我不知道汪律师为什么突然会朝我要这么多现钞,他只说了急用他会跟梅总解释,我没有提出过多的疑问,因为伯母曾经交待过我,汪律师有一次性从公司提走不超过五百万的现钞的权利。
根据汪律师的要求,由我陪他去银行提了款。开车送他去机场后,我顺便拐道去了阿航的施工场地。
“你不是说从湖北来那人是个好帮手吗?人呢?”阿航的确很忙,他正指挥着一帮工人搬运石料,灰头灰脸。
“去秋生那儿了,城哥,这里又脏又乱的,咱们还是去办公室谈吧。”阿航取下安全帽扑打着身上的尘土赶紧拉我离开工地:“多不安全,这里的木板石头可不长眼,伤了你的话任大小姐还不活活吃了我呀!”
“秋生要装修吗?没听说呀!”在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我叫他赶快洗脸好一块出去。
“不是装修的事。待会去哪儿?”
“我在南洋宾馆订了房间,今晚谁也跑不掉。”秋生不装修他找那人干嘛?我正要问他,电话响了。
挂了电话,阿航告诉我是秋生打来的,“正好秋生说要感谢感谢你呢!你没带手机吗?他说打你电话不通。”
“早坏了,还没修好,他谢我什么?”
“去了你就知道,这下你今晚可以省一顿饭钱了。”
天下还有这等好事,“唉,有你们这些朋友在,我想请客掏自己的钱都这么难。”我叹着气摇摇头乐哈哈关上了车门。阿航说:“城哥,其实你今天不来我也正想找你呢!早想出来大吃一顿,这段时间实在是没有时间, 只怕这样忙下去你我的交情都忙淡了。”
“你说这人是不是做起生意来眼里都只剩下钱了?”
“不知道,反正我不是。你说的对城哥,爱是两个人的事,现在有了路青云后,我的整个胸口天天都是满满的,即使关紧心里那扇窗也觉得浑身是劲。”阿航叹道:“有个人爱真的很好!”
我的胸中顿时烧起一团火,是嫉妒吗?不,是失落。我们的目光平静地相对在后视镜里。每一次看到阿航这幽黑发亮的双眸这高挺挺秀直的鼻梁这立体泛红唇线分明的嘴唇这光滑如雪嫩似水晶的小脸,我都会想起多年前的那个黑夜,那个晚上真的好冷,那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哥,抱抱我吧!好冷!”
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黑就有人喜欢白,有人喜欢红就有人喜欢蓝,阿航以前曾给我说过他喜欢蓝色,因为在香港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蓝色好像是个谜,蓝色代表着忧郁,从那以后他就把蓝色当成了他的本命色,阿航还说他最喜欢在晴空万里的午后踩着维多利亚的细沙滩去看海,说着说着,阿航又闭着了眼,仿佛已经置身到了那个梦幻的世界:“那时候,海天一色,我头顶的天是蓝的,我眼前的海是蓝的,城哥——”阿航叫我:“每当此时,我真希望我的灵魂能跳出躯体,我想看穿我的身子,我想知道我整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了蓝色?”
“我不知道。”我一直都是这么回答他。我知道他在暗示我什么。我说段左航,如果说善良的人个个都是天使,那天使从云彩里掉下来的时候也是有些头先着地有些脚先着地,脚踩着地的成了凡人,他们要结婚要成家要生孩子要过日子要平平淡淡要劳劳碌碌,比如说我,而你肯定是头先着地那种,这就注定了你在着地弹起后还要扑闪着翅膀继续飞翔,既然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为了找回生命里的另一半做个完人,那你就飞吧,阿航,我只希望你停在云端站在风尖踩着浪头踏上峰顶休息的时候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背上那展开的湿淋淋的翅膀,我相信你会明白为什么你总是叫累叫苦总感觉寂寞孤独,“阿航,我们都是单翼天使,想立足人世间哪能找个一顺边的翅膀?”
“这些道理我都懂。”每当我说起这些,阿航总会双眼不离蓝天然后长叹一声:“天是蓝的我的男的,我爱蓝色,这是宿命!”
“城哥,想什么呢?”阿航拍我的肩:“开过了!”
可不,走了一下神,南洋宾馆跑车后了。
说是好好聚聚其实也只到了秋生。跟在秋生身后那人也算老相识,就是我给阿航介绍那船夫,至到今天我才知道他的大名叫戴卫国。加之阿航和我,统共四人而己。谁说四人就不能订个包房大吃一餐?
“戴哥,你好!”我朝他伸出了手。
“夜先生别这么客气,没有你我只怕还要在千岛湖上划船一生呢!”他极憨实地把手在身上擦了又擦紧紧抱住我的手:“叫我卫国吧!”
卫国,保卫中国,一听就知道是随着新中国而诞生的根正苗红的庶子忠民。卫国很瘦很黑眼窝挺深,他结实有力的大手告诉我他的确经受了生活的所苦所累,他清苦的面颊仁厚的下巴他饱含精神的双眼感激着我的知遇之嗯,他没多说话,他想说的我从他经久不愿松开的手心里早己感觉得到。我拍着他的手背叫他坐下:“好好干!”我鼓励他。
“现在见你们俩都这么难!”我埋怨着白了阿航和秋生一眼,我招过服务生:“点吧,我请客。”
“可别,说好了我请的。”秋生叫服务生到他跟前:“来四份鲍鱼饭,待会找我结帐。”他指指我警告道:“今天谁跟我抢我跟谁急。”
“放心好了,我的钱包比脸还白。”阿航拿热毛巾擦擦手翻转着看:“我命怎么就这么好呢?秋生一出血我就白吃680块,呵呵!”阿航叫服务生再加一份:“一份吃不饱。”他把头凑近卫国:“拖你的福了。”
原来,秋生要扩展生意,进货量很大,他在飞虹手机行附近设了一间库房,这么贵重的东西跟堆了一屋子钞票有什么区别,正苦于没个可信的人作仓管,恰好卫国来石家庄后也一直放心不下留守家中瘸了一条腿而无人照料的老父亲,阿航听说后大义凛然做了个利人利己的顺水人情。今儿卫国跟秋生一起去车站把人给接了过来。
“我爸虽然瘸了条腿,可是写写算算还不在话下,总之我谢谢你们仨。”卫国很高兴:“他行动不方便所以也没让他跟来,我替他敬你们一杯。”
“咱们一块干吧!”我起身给大伙倒酒:“今儿可得好好喝两杯。”我把倒满的酒杯推给秋生一个:“你先请?”
“哪儿买的?”秋生拉着我的手腕,他指着我戴在手上的表很惊讶:“你现在这么大款?”
“几百块而己。”阿航打掉秋生抓住我的手:“喝酒吧!”
“我隔壁也是一家外贸店,专卖世界名牌,有一天我进去逛时也看中了这一款,一问价,我掉头就走。”
“那是自然的,你经常要出席高官晏会,戴这个多寒酸。”
“寒酸?哥哥,七十几万哪!”秋生一扬头咕咚一声下肚,他咧着嘴喷着酒气:“我得卖多少手机才能挣得回来?”
真有这么贵?我可不敢要。我看看阿航,阿航抬起胳膊给秋生看:“我也有!四只眼都看不准,他那只是我送的,全是仿制品,等着你给咱兄弟买正宗的呢!”
“我买不起。”
“死心眼,说两句好听的哄哄人不行啊!”
“这可不行!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落地都有声。”
他俩又斗起嘴来了。
呵呵,我只有笑,我喜欢这种场合,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喜欢听他们不太噪杂极似英语朗读柔润的潺潺声一样的伴嘴,我发觉我们又回到了早已远去的学生时代,那年月,在我眼前经历过的每个人,哪怕是一个平静如水的侧面,哪怕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回首,哪怕是躲在某个黑暗角里的默默凝视,都会有太多的故事都会给我留下太多足使我彻夜不眠的回忆和思考,好也罢赖也罢,日子总算如抽丝般过去,过去了,我知道那一切都只能尘封在我这一生的记忆中,好在如今我们庆幸彼此都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都有着一块送往嘴边可口与否只有自己清楚的牛排,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发展,我们每天都在开拓进取,自然是各自为政聚少离多以至于终日不见,既然没有人可以拒绝时光的匆匆没有人可以改变日月的轮回没有人可以报复岁月的沧桑,那我只有守住可能会喷出千言万语伤人的嘴巴来学会微笑,伯母说了开心的时候要笑伤心的时候也要学会笑,要笑出包容笑出智慧笑出胸怀。笑多了笑久了,摸摸脸照照镜,我竟笑出对酒窝来,真收获不小。
“哎——”秋生敲打着手中的刀叉提醒我:“那家饰品店的老板长的很像星缘以前的小涵姑娘。”
“哦,是吗?”我停下入嘴的勺子。
“我去过她店子里两次,再加上跟小涵也不熟,没搭话,不敢说她一定就是小涵,不过她可比小涵要漂亮。”
我的眼前忽地跳跃着小涵那双极具灵性的纤纤细手。多美的指尖舞!多美的小涵!小涵,一年不见,你就翅硬羽丰衣锦还乡我们由衷为你高兴,我们都以为你的归来会暖热洪流那颗冷寂的心,知道吗小涵?我也是无意之中得到了代表你的那串号码,洪流如获至宝,打过去洪流说他很伤心,再打过去是盲音,最后一次当洪流没抱任何希望按动那几个数字后,他告诉我成了空号,小涵,你难道真的忘记了昔日与你一同作战的这帮同事好友还是,还是你另有苦衷?我情愿相信后者。
“瞧瞧瞧瞧,一说起她你眼都直了,换个话题吧。”阿航转脸问卫国:“你爸的腿怎么回事?有得治吗?”
他可真会收买人心。
“说来扫兴。”卫国端起桌上的冰水漱口:“以前他有几个臭钱的时候,跟着一帮猪朋狗友花天酒地到处惹祸,一年到头不回家,更可恨的是他还跟我妈离了婚,去年他和朋友来北方做生意,不知怎么搞的,可能是赔了吧,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成这样,狼狈极了,从那以后整个人都变了,话少了酒也不喝了,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也不说,只知道摇头叹气,没办法,我才从工地辞了职到千岛湖上摆渡,离家近可以照顾他。”
“你真是孝子!”我庆幸没有看错人。
“再怎么恨他,我也是他儿子,工作也好老婆也好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他作为我父亲这一事实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也是不能选择的,不过这样也好,人一穷就没那么多歪心眼,踏踏实实过日子有什么不好!”
“有你这样的儿子是他的福气。”我们都这样安慰卫国:“放心吧,以后慢慢会好起来的。”
饭后,卫国随阿航回了工地,我开车送秋生回家。
“其实今天你不找我,我也会约你出来的。”他打着饱隔靠着皮坐椅后背随着轻柔的音乐双脚极有节奏。
“都会这么说!”我给了他一个撇嘴。
“伯母还没信儿?”
“这还用问吗?”
“快了!”
我猛地踩住刹车扭头看着他那油光发亮充满智慧的前额——我在等他的下文。
“我表哥说伯母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案子,上头瞒得很紧,估计是经济方面的纠纷吧,省里的一把手亲自给她跑事,快回来了。”
这就好!经济纠纷顶多属于民事范畴,我还一直担心伯母会给刑事案子扯上边。这就好!我给了秋生一个感激的微笑,对他的话我是深信不疑的。我终于可以弹出支烟舒心地抽上一口了。
打开车窗,我抬起头看看天上银光闪闪像巴镰刀的月牙儿,它时隐时现正羞羞答答收割着层层乌云,相信明天一定会是艳阳高照。想到这儿,我的欢乐又悄悄爬上了眉梢。







![[Virile]超人气台湾健身教练Goat私房摄影111p+视频-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7043916.jpg)
![[BL游戏][PC][RPG]梦境之末2.0正式版[R18]-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5719857.jpg)
![[JQVISION] 调教Big黝黑肌肉体育生巧克力男孩[136p]-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6060221.jpg)
![[谢梓秋]2021最新型男私房摄影BODY STYLE[81p]-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10/1634223014-101414501480-e163422308846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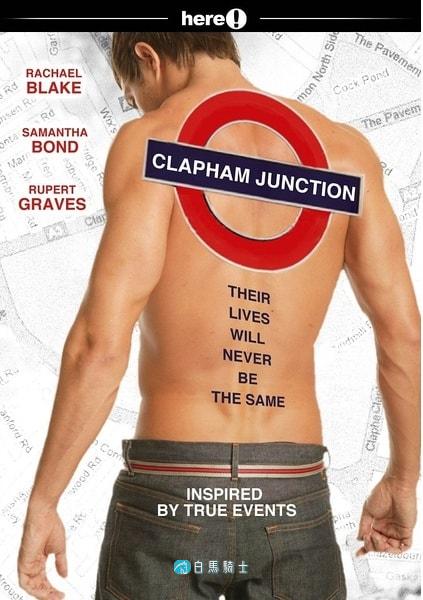

![[BLUEMEN]蓝男色NO.200 超人气体育男神允硕全见版-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6077725.jpg)
![[1083张]惊人超大24cm,美混血帅哥网红李亚斯私照流出-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1/1632828731-092811321143.jpg)


暂无评论内容